编者按: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曾合力主持“古工委”工作十余年,又分别将四家古籍出版名社带到新高度,既是出版行业变迁的见证者,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践行者。近日,由他们合著的《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联合出版。《上海书评》特此发表本书四人“同题共答”代序,分为上下两篇,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四位“古籍出版掌门人”如何边学边行、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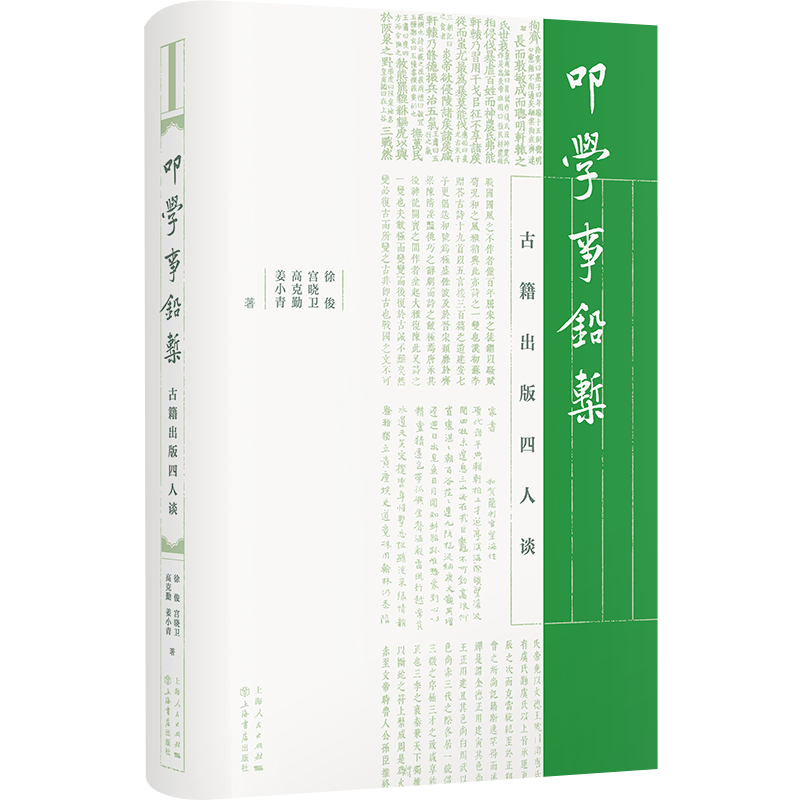
《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参加“2021-2035年国家古籍规划”工作专班留影,左起:姜小青、徐俊、高克勤、宫晓卫。
古籍行业,难忘的人与事
戎默:四位老师都在古籍出版行业工作了三十年以上,并都各自主持过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很长一段时间,见证了古籍出版行业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与辉煌。请首先谈谈你们各自的工作经历,及从业以来难忘的事件与人物。
徐俊:我1983年暑期大学毕业即入职中华书局,因为我本科毕业就工作了,所以比三位仁兄都早。我们79级赶上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相对于“文革”前的“老三届”,有所谓“新三届”之说。我们四位都是“新三届”。八十年代进入出版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的起起落落,社会和行业变化之大,笼统地用当下出版业的视角看过去,其实已很难得到真切准确的认识。我入职之初的出版业基本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古籍出版发展滞后,即使到九十年代初,我所在的中华书局还基本没有沾过市场经济的水。这就导致在后来被迫跳水的时候遇到的风浪险滩就更多,回想起来,虽然一直在同一个单位日复一日干着几乎同样的工作,但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还是林林总总一言难尽的。有幸的是在自己出版生涯的后半段,行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又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与同事、同道、同行一起,经历了古籍出版业和所在出版社恢复发展的阶段,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美好回忆。从我做编辑的经历来说,给我触动最大也最难忘的是1985年接手文学编辑室编务工作后,从书稿档案看到的周振甫先生《管锥编》审稿意见和王仲闻先生《全宋词》审稿记录,深感震撼。一方面让我对编辑工作有了真切的感知,另一方面让我对前辈编辑家以及书人书事有了持续关注的兴趣。从我经历的出版事件来说,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给我触动最大的还是2006年11月26日《于丹〈论语〉心得》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刷新了我对传统文化读者需求的认识,让我们坚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探索的初心。
宫晓卫:我是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进的齐鲁书社。当时这是一家新兴的地方古籍出版社,充满活力,声誉正隆,其传统文化出版方向符合我所学专业。于是在我毕业决心离开上海回山东时,选择了这家社。从此结缘出版。
我的古籍出版从业经历可从两方面说,一是编辑出版,一是与古籍出版行业平台的交集。
编辑出版的经历大致划分三个阶段:一是1985年到1994年初,在齐鲁书社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二是1994年初到1997年初,任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副主任;三是1997年初到2015年3月,任齐鲁书社社长。在出版社当编辑的时段,正赶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图书出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震荡期,出版开始尝试着向市场要效益。作为入行不久的新编辑,那股积极探索和倾力策划的干劲,是迸发出来的工作状态,至今难忘。回想当年我在古典小说、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影印书等方面提出的选题创意和策划,进入市场的图书都有过不俗的效益回馈,让自己有了一点编辑职业的自信。那时特别感念自己遇到了一些好同事,大家共同谋划,互相帮衬,很享受职业的快感。同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陈学振先生。
清楚记得自己曾作为本系统图书出版“两个效益奖”的得奖编辑代表登台发言,发言中有一节专门讲到出版社一个明白的领导对编辑成长的重要性,没有社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果断拍板,编辑提出再好的选题,也会胎死腹中。这里感慨和感谢的社领导是时任齐鲁书社社长陈学振。陈学振先生到齐鲁书社前是山东出版总社研究室主任,在齐鲁书社内部管理混乱之际,他临危受命任该社社长,挽危局于即倒。齐鲁书社古代小说标志性的出版物《明代四大奇书》和“小字本”古典小说系列,都是在他任上面世的。即便他升职离开齐鲁书社,还鼎力支持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重大项目在社里的出版。对这样懂行的老领导,我一直心存敬意。
我在山东出版总社总编室只工作了三年。因工作分工分管本系统的图书选题、图书质检和编辑培训,是个开阔眼界、加深理解出版的时段。从中得到的经验,反哺此后自己对一个出版社的驾驭,深感有益。
1997年我回齐鲁书社任社长,面临的是本社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危难局面,艰难程度远超以往,这在收入本集的多年前对我的那篇访谈里略有提及。难熬的日子刻骨铭心,好在我和我的团队用较短时间破解了困局。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好书,经济效益连年增长。到我离任,这个单位获得过一些图书大奖,出版形象端正,而且选题储备充实、利润稳定、资金充足,家业已称得上兴旺殷实。
另一方面是与古籍出版行业平台交集的经历,于我来说比较特殊,它几乎贯穿了自己整个职业出版生涯。下面的对答要谈“古工委”,这节经历就放在后面说吧。
高克勤:1986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由于我读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专业,读的书多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早就向往这家出版社,所以毕业时没有选择在高校任教,而是如愿来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编辑。
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培养新进编辑的惯例,安排我先进校对科实习半年,然后被分配到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为主的第二编辑室做编辑。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设五个编辑室,其中文学编辑室有三个,共有三十多位编辑,这也显示出对古典文学的重视和古典文学专业编辑队伍的强大。第一编辑室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典籍整理著作为主,第三编辑室以编辑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为主,还有历史、哲学各一个编辑室,各有十位上下的编辑。
进社二十多年来,我经手审阅、出版的书稿不下数百种,内容以古典文学为主,并旁涉历史、哲学、宗教和文物收藏,等等,远远超出了自己大学时所学的专业范围。记得进社后审阅的第一部书稿是四川大学教授项楚先生的《敦煌文学丛考》,第一部编辑出版的图书是复旦大学教授陈允吉先生的《唐音佛教辨思录》。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今的学术名家,而我担任责任编辑的这两部书稿均是他们的第一本论文集。当时室主任把这两部书稿交我后就让我自己独立审阅并发稿,虽然这些论文均已发表过,但我也不敢懈怠,而是仔细核对引文,并在体例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浅见,得到了作者的认可。这两部著作后来分获全国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和国家教委优秀成果奖的一等奖。
作为新进编辑,我在编辑室长期兼任编务工作,直到1992年底由新进编辑接任。编务是一项琐细的工作,负责编辑室发文、发稿的登记以及回复读者来信等事务。1993年1月,社进行科室调整,文学编辑室整合为一个编辑室,即第一编辑室,由李梦生任主任,王兴康和我任副主任。原第一编辑室主任赵昌平时已任副总编辑。李梦生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1年入社工作。他对明清文学和中国古代小说都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后调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社长。赵昌平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2年入社工作。他对唐代文学有精湛的研究,1994年3月任总编辑直到2013年4月退休。他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王兴康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1985年入社工作,2002年12月任社党委书记、社长。他善于策划运作重大出版项目,长于经营,为出版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与他长期在一个编辑室工作,先后继他出任第一编辑室主任和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兴康后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他们三位都年长于我,都是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又善于经营管理的杰出人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前二十多年间,我与他们三位长期共事,先后接受他们的领导,耳濡目染,领悟他们的出版理念和工作作风。
1997年3月,我任第一编辑室主任。2000年1月,我被任命为总编辑助理;同年12月任副总编辑。次年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挂职任版权管理处副处长近一年。2005年9月兼任副社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的前二十多年间,我从编辑做起,直到担任副社长、副总编辑,管过出版社所有的生产经营部门,了解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
2009年12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调我出任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当时的远东出版社管理比较粗放,经营亏损。我到任后,在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社员工的支持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远东出版社扭亏为盈,职工收入有了接近一倍的增长。
2013年初,集团调我回上海古籍出版社主持工作。之后近十年间,我带领全社员工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坚守古籍出版专业,努力维护和打造专业品牌,守正创新,踏实工作,出版社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社会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回顾自己的工作经历,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给我提供了成长和施展才能的平台,我也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和全部的才智奉献给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前辈传给我的接力棒完好地交给了下一任。因此,在退休时可以无愧地说:我尽力了!
姜小青:我是1991年7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江苏省人事厅分配至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的,之前是想考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博士的,也报了名,还给王先生写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记得王先生回信说,要准备好政治和英语,并寄了两份以前的英语试卷,后来由于个人原因,从济南赴上海考试途经老家镇江时提前下车,做了“逃兵”,工作以后见到王先生,一直没勇气再提这事。到古籍出版单位工作,可以说并不是自己主动选择。一开始先在文学编辑室做编辑,第一感觉就是在读书期间敬仰与慕名的许多大学者,都是我们编辑室的作者,如钱仲联、唐圭璋、程千帆、霍松林等先生,再看到编辑室主任吴小平、副主任卞岐,与这些学术大家自如交往,不免心生羡慕,他们一位是姜书阁先生弟子,一位是卞孝萱先生哲嗣,有很好师承和家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都在《文学遗产》发表过论文,但到出版社以后,对编辑工作十分热爱,我便暗中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老师和榜样,他们对我更是多方面关照和提携。后来我被调到出版社新组建的期刊编辑室,当时我们出版社有四份期刊,两份自办:《古典文学知识》《民国春秋》,两份合作办刊:《文学遗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典籍与文化》(与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我除担任《古典文学知识》《文学遗产》责任编辑外,还负责《文学遗产》编务,主要是与文学所对接,这项工作使我对编辑工作又有了新认识,徐公持、吕薇芬、陶文鹏等编辑部老师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平等待人的谦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社科院大楼七楼,六七人挤在一间屋里办公,每次去,都见他们在安静审稿,讨论稿件也都心平气和,对我们出版社推荐的稿件,既尊重也讲原则,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封主编徐公持先生对出版社推荐稿的退稿信。他们对我这个三十刚出头、对编辑业务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关照。李伊白老师不仅帮助订住处、返程票等,还自掏腰包请吃饭。这件工作持续了六年。1997年,我进入出版社领导班子,任总编辑助理,2001年任副总编辑。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2003年7月至2018年10月,我主持凤凰出版社工作,开始任命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后来任主持工作的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对于这十五年,特别是前期工作,我不太愿意回顾,有些事甚至不堪回首。前两年,凤凰集团总编辑徐海兄约我,为他在《文艺报》主持的专栏写文章,推脱了几次,后来勉强写了一篇,就是收在这本集子中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凤凰出版社更名前后》,许多难忘甚至痛苦的经历并没有写,也没法写,文章发表时,徐海兄将文中的“不值得,不后悔”六个字作为题目,真深知我心。我2018年底退居“二线”后,专任凤凰集团江苏文脉整理研究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持江苏省重大文化工程“江苏文库”出版工作,2021年5月退休后返聘,继续担任上述职务和工作。2024年5月返聘到期,虽然上级仍希望我继续接受返聘,但自感力不从心,故知所进退,彻底告别职场。
在三十多年古籍出版职业生涯中,要说难忘的人和事,确实有很多,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出版社前两任社长高纪言先生、薛正兴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离、退休后,在没有任何名利情况下,坚持工作到生命终点。高纪言先生去世前几个月,抱重病从医院到《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最后一次审稿会现场,薛正兴先生在生命最后一天,听我谈拟接受《子海》选题设想并予肯定和指导,这两个场景,是我终身不会忘的。我时常会想,他们为什么如此,但真的没有答案。
“古工委”的种种
戎默: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工委”,发轫于1986年齐鲁书社承办的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会,于2008年正式成立。是全国古籍出版单位加强互相合作、交流行业信息、联合集体发声的行业协会,对国家的古籍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四位老师作为第二届“古工委”班子成员,于2013年至2024年主持“古工委”工作十多年,想听听各位老师谈谈“古工委”。
徐俊:“古工委”作为全国古籍出版行业协会已经存在四十年,经历了“古联体”和“古工委”两个大时段,它的前世今生,晓卫兄、小青兄了解多。因为中华书局是“古工委”主任单位,有多位领导在其中任职,所以早先我参加“古工委”活动比较少。在“古联体”阶段,1993年10月,我受单位指派去郑州参加过一次社长年会——“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见到了多位业界前辈和年轻社长。那时候会期很长,去了郑州、洛阳、开封,参观了少林寺、打虎亭汉墓、嵩山等,就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晓卫兄,印象中还曾多人同室而居。2013年8月3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在银川召开,会间进行了“古工委”班子换届,新班子由我们四位组成,这一届“古工委班会”主持工作超过十年,一直到2024年1月12日班子换届集体卸任。不谦虚地说,这十年当中大家一起做了很多事,大到古籍出版行业建设(规划、规范),小到每年的社长年会(交流、推优),营造了古籍出版的良好环境,推动了全国古籍出版整体向好发展。在主持“古工委”工作的十年,我信奉老朋友赵昌平先生跟我说的话,古籍出版本身是个很小的行业,如果我们不能团结合作,那在中国出版业就没有我们古籍出版的声音。我们一度自嘲“古联体”是“丐帮”,但我们有抱团取暖、合作共赢的传统,有“古工委”上一届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础,新班子工作一直得到各理事单位的大力支持,加之晓卫、小青二位在前后两届班子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第二届的十年工作顺利,令人愉快而难忘。
宫晓卫:“古工委”是全国古籍出版的行业联合体。其雏形的生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布后,一大批新兴专业古籍出版社涌现,行业迅速扩容,因同行业相近的需求,自然聚到一起的。1986年,齐鲁书社承办了第一次全国古籍出版工作研讨会,古籍出版以此为开端,逐渐形成自己的行业平台,我也开始了与这个平台的交集。1986年会后,古籍社间的联席会多了起来,大家议定行业会议一年一次,其他会议视需要临时定。多年后,一年一次的行业会议定名为“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这个过程,我在见收本集里的《从“古联会”“古工委”说古籍出版四十年》和《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拙文中有简述。
我本人参加会议及相关活动,起初是陪齐鲁书社时任社长(总编)去的,或被单位指派为代表到会;又因1988年我被安排为启动古籍优秀图书评奖的筹办人,除了中间离开古籍社的三年,举凡含图书评奖的社长年会,基本上是每会必到。任社长后,曾任“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简称“古联会”)副会长;2008年9月民政部批准“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改任副主任;2013年“古工委”换届,再任第二届“古工委”常务副主任,直到2024年初换届卸任。
伴行古籍出版行业平台发展的数十年,让我直接感受了同行业各古籍社成长过程中的荣耀辉煌和艰辛坎坷,亲历了期间大部分的重要活动,目睹了古籍社联合初期那些优秀出版人的风采。回望八十年代古籍出版大发展时期的那些先行者,其中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魏同贤、巴蜀书社的段文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高纪言,以及齐鲁书社的孙言诚、岳麓书社的潘运告、三秦出版社的周鹏飞、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孙安邦。各位先生热心服务群体,承办会议,策划合作项目,创办宣传媒体,出点子,拿主意,共同维护了古籍社联合会初期的平顺发展。
2008年“古工委”成立,主任是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李岩先生,副主任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和我,秘书长先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沈致金,后由黄松接任。“古工委”能够成功获批,成为中国版协的专业委员会,由民间团体的“古联会”变身国家正式社团组织,李岩先生起了关键作用。作为第一届“古工委”主任,他带领的“古工委”,氛围和谐,团结协作,成绩斐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对照“古工委”成立大会上原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讲话中对这个组织的期望和要求,这届“古工委”以自己的作为,交出的是一份上下满意的答卷,深得业内外赞誉。
回顾第一届“古工委”的优秀表现,还必须提到秘书长黄松先生。与李岩先生一样,黄松先生也是能力出众、极具亲和力的人。他曾任国家“古籍办”常务副主任,直管古籍整理出版,与业内各社很熟且关系融洽,深受大家敬重。记得在他卸任“古籍办”工作时,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先生高歌一曲《送战友》,发自肺腑,引起了在场同道的共鸣。很高兴他任职中华书局副总经理,没离开古籍出版,又在第一届“古工委”秘书长任上继续展露他的才能。这届“古工委”让大家称道多年的数次组织古籍出版代表团“走出去”,成功到海外出访参展,都依靠他的具体操持。
第二届“古工委”是我们四位这一届,徐俊任主任,姜小青任副主任兼秘书长,高克勤和我任副主任。延续了上届班子成员人数,延续了上届的“班长”、秘书长的才能出众、深得大家信任,也延续了上届“古工委”业已形成的相互尊重、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保持了以往的优良传统。在妥善做好日常工作之外,围绕新时代对古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主动谋划,建言献策,如筹划举办纪念古籍小组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新时期古籍工作研讨会等一系列专题会议;参与相关政策文件拟定的讨论;受“古籍办”委托,有效地落实了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版本相关工作的协调组织;班子成员四人作为“2021-2035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制订专班成员,配合“古籍办”完成“规划”的摸底调研和制订等,充分发挥了“古工委”作为行业社团的重要作用,突显了本行业的职业素养和精神风貌,提升了行业声誉。
本人从业数十年,经历的社团不算少,仅以个人感觉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古工委”,这个团体都是出色的。正如提问所说,古籍出版联合平台的形成,特别是“古工委”的成立,确实起到了行业“加强互相合作、交流行业信息、联合集体发声”的作用。行业自发搭建联合平台的初始意愿,不仅由此得以实现,“古工委”作为一级专业社团组织,又切实担当起了国家管理机构得力助手的义务,是协助国家“古籍办”推动古籍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社会团体。
高克勤:“古工委”是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大家庭,有着精诚合作、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按照“古工委”的章程,中华书局为主任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副主任单位。2013年8月2日至4日,第二十八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2012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在宁夏银川举行。同期召开了“古工委”换届会。由于在这之前的201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徐俊任中华书局总经理;2012年12月5日,中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委员会任命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所以徐俊与我在这次换届会上分别接替了前任的职务,徐俊为第二届“古工委”主任,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为常务副主任,我、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为副主任,姜小青后来还兼任秘书长,组成了“古工委”的班子。没有想到我们这一届班子居然做了十多年,这可能在“古工委”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吧。“古工委”的工作主要是每年举行一次社长年会和不定期地举行专题研讨会,聚焦大家共同关心的行业问题进行交流,找到解决的方法;对上一年度出版的古籍专业图书评奖;完成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中国出版协会交办的任务。由于我们四位年龄接近,专业相同,都长期担任各自出版社的主要领导,所以有许多共同语言,不仅每年共同筹划并参加“古工委”的社长年会,而且还因为工作原因如参加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等不时会相遇;我和宫晓卫、姜小青在任时还参加每年一次的华东地区古籍图书评奖会。特别是2021年,受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委托,徐俊、宫晓卫、姜小青与我组成专班,参与古籍规划的制订,仅上半年就三次去北京参加评审会,有两次都是连续三天的会议,朝夕相从。在共同的工作中,怀着共同的目标,我们四人确实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甚至不约而同先后取了斋名。
姜小青:关于“古工委”历史,宫晓卫社长在本集文章中有详细论述。我第一次参加“古联会”会议,是1998年由辽海出版社承办、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记不清是第几届了)。2013年换届,我被选为副主任,后来又兼任了秘书长,直到2024年初换届。
这十年,我有幸见证了古籍出版行业快速发展,特别是专业古籍出版社,从最初对市场经济不适应甚至排斥,到积极探索适合各自单位发展的有效路径;从一味强调古籍图书特殊性,到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市场;从要求放开图书出版分工政策,到立足自身,在坚定专业化的定位中创新发展;从过去举债经营,到现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效益越来越好。从“古工委”每年一届优秀图书评奖可以看出,各专业古籍出版社都有自己特色和优势内容生产板块,许多学术价值高、文化影响力大的项目,都是持续多年甚至几任出版社社长。我粗略统计过,“2011-2020年”“2021-2035年”两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古工委”会员单位,特别是专业古籍出版社申报和入选的项目占了相当大比例。“古工委”有一个好传统,为加强会员单位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合力推进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每年会举办两次工作会议,一次是1月初在北京中华书局,主要请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领导讲形势、提要求,目的是提高会员单位对做好古籍出版工作的认识和站位;另一次是举办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至去年已举办三十七届了,每次会议研讨主题,由“秘书处”会前听取各会员单位意见,并经“古工委”班子研究后确定,因此都是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每一次交流发言文稿,“秘书处”都会提前编印成册,作为会议材料发给大家。社长年会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举办上一年度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评奖(推优),会员单位根据要求,提供参评样书、专家推荐意见和编校检查记录,采用匿名评审。多年来,“古工委”评出的优秀古籍图书越来越得到学术界关注和认可。
除上述会议,我们这届“古工委”班子,还组织过两次比较有影响的会议,值得一记。一次是2018年8月28日,借在昆明举办第三十三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之际,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除邀请了柳斌杰、杨牧之等领导,还邀请了杨忠、严佐之、金良年、荣新江、杜泽逊五位古籍小组成员,他们的精彩发言,引起社会广泛反响,提高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社会关注度。另一次是2021年10月16日,在成都召开了“新时代古籍出版工作座谈会”,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颁布四十周年,邀请了版协理事长邬书林参会,会议采用重点发言和交流发言形式,效果很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对两次会议都做了详细报道。另外,我们四人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6月,作为国家“古籍办”“古籍规划编制工作专班工作小组”成员,参与了“2021-2035年国家古籍规划”前期调研以及评审相关组织工作,切身感受到国家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感受到评审专家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也感受到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者积极参与的热情。
2024年1月10日下午,“古工委”换届,我们四人集体卸任。这天上午,我代表“古工委”最后一次参加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会议,获“2023年度优秀专委会奖”表彰,算是画了一个圆满句号。从个人来讲,这段“古工委”工作经历,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记忆。换届第二天,我找出若干张四人不同时期的合影,发了一条微信:“‘古工委’2009年1月成立,2013年9月换届,其后徐俊、晓卫、克勤我们四人组队十年,为同行服务,并见证了这十年古籍出版事业发展,昨天顺利换届。我们四人彼此间相识二十多年,特别是这十年在班长徐俊兄带领下并肩前行,结下了兄弟般情谊,感恩和祝福兄弟们。”
初次相识何时,彼此如何评价
戎默:四位老师过去几十年来都在同一行业内工作,又在“古工委”共事十多年,有很多交往,甚至可以说情谊深厚,想请你们各自谈谈与对方的初次相识及对对方的评价。
徐俊:前面已经说到1993年郑州年会第一次见到晓卫兄,晓卫兄那时已经是齐鲁书社总编室主任,而齐鲁是八十年代最早成立的古籍出版社,在业界有很大的影响。我当时是中华书局文学室副主任,很少出差开会,郑州年会会间大多与北京同行的几位同龄人聚在一起,跟大家没有什么交流,但晓卫兄山东大汉的高大形象留给我深刻印象。与小青兄神交已久,最早见面是在北京建国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因为《文学遗产》杂志先后由我们中华和凤凰出版,都被邀请参会,我们很远挥手打过招呼。除了古籍出版同行,我们还都是“镇江籍出版人”,又因《镇江文库》《镇江通史》而时常碰面。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中华书局的“对标”单位,因此可以说克勤兄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我们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是79级,都读中文系,同一张卷子考上大学,是旧时候所谓的“同年”;进入出版社之后,我们都在文学室,后来都做文学室负责人,再后来基本同期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总经理,甚至我们两人对所在单位出版史的兴趣都难得的一致,点灯熬蜡写了不少各社的书人书事。与克勤兄不同场合见面,其中较早一次是在北京站,他们班毕业十周年在北京聚会,陈尚君老师是他们指导员,是我的作者,我去北京站送陈老师,因此见面。我从上古历届领导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克勤兄更是我一直追慕学习的对象。以上是我记忆中最早的点滴印记。我们相处久了,互相了解深了,感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很难用一句话来评价对方。晓卫兄比我们年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生长于孔孟之乡,在我看来他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现实化身。小青兄兼任秘书长,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小青兄的擘划联络。他待人诚恳,深受各成员单位爱戴。克勤兄为人诚恳,处事务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我们二人同游华山湖,克勤兄25分钟登顶华不注,逐级数过去共829级台阶,而我只有在山下为他拿外衣的份,惭愧。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他们的性情,晓卫兄的“厚”,小青兄的“诚”,克勤兄的“勤”,都是最值得我学习的。不甚妥帖,言其大概吧。有句话说,“所谓朋友,就是一群经常见面的相同的人”,“相同的人”是关键。退休后,各种机缘我们仍然经常见面,一群先后从出版岗位退下来的老朋友聚在一起,“相识在少年,相聚在年年”,人生何其幸也!
宫晓卫:我们四人都是古籍社编辑出身,同行的关系,我和三位老友认识都有二三十年了。与徐俊兄的认识,是在1993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承办的古籍出版座谈会上。他是中华书局参会代表,我则陪同本社社长到会,都是同龄人,很容易相识。与克勤兄认识得更早,应该在他1986年毕业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久就知道他了。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与我师兄王兴康(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一个编辑室,当年我几乎每年都到上海出差,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必到的点。到了社里一定会去看望师兄,于是知道了克勤兄是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研究生,至于初次见面的具体时间,倒是模糊了。最初知道小青兄,是从江苏古籍出版社老社长高纪言先生那里听说他们社里新进的编辑里有位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当年我和高先生很熟,常在古籍社活动时见面,高先生是山东人,我们算是忘年交。巧的是我和小青兄的研究生导师于维璋先生认识,有一年参加山东省古代文学学会年会,我们还同住一个房间,话题里自然少不了与我已是同行的他的学生姜小青。太熟悉了反而让我忘了我们初次认识的时间,印象深刻的是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承办首届华东古籍评奖会,他到车站来接我,那时他已是社长助理,我们见面时感觉已经很熟络了。
我们四人彼此加深了解,还是在各自任自己单位主要负责人后,因在同一个行业平台,更因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每年都会见面。尤其是我们同为第二届“古工委”成员,因“古工委”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头。长达十年的愉快合作,形成了彼此间密切的关系,有着兄弟情谊。
他们三人有着共同的特点,品德端正、热情敬业,思维敏捷、思路开阔。作为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具有出色的经营组织管理能力;作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人,他们又都有深厚的学术根底,有典型的学者气质。两者的结合,都极好地体现在他们带领的出版团队创出的杰出业绩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始终是古籍出版行业公认的带头大哥,徐俊、克勤执政的阶段,又都百尺竿头,创出新的辉煌。小青领导的凤凰出版社,从他接手时员工不足二十人,由他一路带成了行业翘楚。而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学者风采,在学术界、行业内都是有口皆碑的。
他们三位是南方人,有着温良细腻的共性。克勤性格更见谦和沉静,徐俊、小青则是平和中不失豪气。我们四人搭班子,合作起来同频共振,十分默契。当年经常会听到行业内外朋友对我们四人合作的称许,我认为是自己“遇对了人”,这是由衷的。
高克勤:在我们四人中,宫晓卫最年长,也是我最早认识的。晓卫兄本科、研究生都高我一届,也比我早一年到出版社。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的研究生,与王兴康是同门。我进编辑室时就从兴康兄那里得知了他的情况,最初的相见可能就是他来我社的时候。晓卫兄为人大气、豪爽,做事明快、利落,做事周到,待人热情。他是齐鲁书社的老社长,担任社长长达十九年,为齐鲁书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是“古工委”的老领导,是我们四人中唯一一个经历了“古工委”从筹办到成立发展的全过程的人,对全国古籍出版界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办会经验丰富,总能大处着眼,每年社长年会的筹办都能得到他的指点。轮到齐鲁书社做东道主办会的时候,总能感受到山东人的热情和豪爽。
姜小青长我一岁多。记不清是何时与小青兄初次相见的,应该是在哪年的华东地区古籍图书评奖会吧。小青兄为人谦和,待人真诚,说话风趣幽默。很佩服他能迎难而上,始终坚守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使凤凰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选题在全国同行中名列前茅。他是“古工委”的“大管家”,主持“古工委”秘书处的工作,不计得失、不厌其烦地每年要做筹办社长年会的大量工作、撰写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规划,及时传达落实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中国出版协会的有关指示精神,为全国的同行服务,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犹记得在“古工委”任上的每次社长年会召开前夕,我们四人都会在小青兄的安排下一起去会场检查的情景,深深体会到小青兄工作的踏实、认真和细致周到。
徐俊与我都是1979级大学本科生,算是同年,不过他大我几个月。他1983年本科毕业就进中华书局工作,是我们四人中从事出版工作最早的。在我们四人中,我与徐俊兄相识最晚,但彼此相知很早。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时的指导员陈尚君老师的书稿《全唐诗补编》由他担任责任编辑。当时他与我担任各自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陈老师说有机会介绍我俩相识。我与徐俊兄初见是几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图书订货会上,当时我俩是各自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我俩来往密切还是始于在“古工委”共事。熟悉之后,居然发现彼此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不仅履历差不多,而且关注点也多相同,例如我俩都热爱各自的出版社,都有传承弘扬前辈传统的自觉意识,都注意挖掘出版社史料,写了这方面的不少文章。徐俊兄是中华书局的老大,也是“古工委”班子的老大,始终有大局意识,为人谦和,待人热情,乐于助人。我特别佩服他的还有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坚持,他在敦煌学研究和书法方面的造诣为业界羡称。
姜小青:现在记不清与他们三人相识的具体时间和场合了,但大体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1998年第一届华东地区古籍图书评奖会在南京举办,我去车站接了宫晓卫,他其时已任齐鲁社社长。那时,徐俊、克勤和我尚未主持出版社工作,见面和联系并不多,记得也是九十年代后期,徐俊来我们社,他与时任我们社总编辑吴小平中午“豪饮”场景,我虽未亲见,但事后被大家笑谈了好一阵。去年清理办公室时,发现一本克勤签名赠《王安石诗文选注》,上古社小开本,好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可能因我其时正担任《古典文学知识》责任编辑,他作为作者,建立了联系。从认识说起,彼此应该都有二十多年了,但我们之间真正建立广泛联系,还是从2013年“古工委”换届开始。
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学术水平,我都一直视他们三人为榜样,这不是谦虚,晓卫是老大哥,“出道”早,1997年初即任出版社社长,直到2015年才卸任,似乎是古籍社中任社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特别是他与所有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创始人都熟悉,了解地方古籍出版发展历史,我们在一起商量工作,他能溯源历史。他是“古工委”创始人之一,热心这项工作,亲和力也强,所以在“古工委”得到“德高望重”的赞誉。我们都参加了徐俊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组,在研究中可以看出,晓卫1997年任社长时,是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最困难阶段,在齐鲁书社走出生存困境过程中,他的付出,其他人是很难想象的。
徐俊出身中华书局,是我们四人中入行最早的,起点高,见多识广,考虑问题周全,敢担当,“古工委”工作中,凡遇难事,都由他出面;但他为人低调谦虚,从未见他在同行面前以中华书局掌门人和学者自居,每每会员单位有困难或需求,他总是想办法帮助解决。对于“古工委”秘书处工作,他给予我充分信任。我在为其《翠微却顾集》写的书评中,有这么几句:“他本人在中华书局‘内在的职业品格传递’中,成为继上述前辈之后‘学者型编辑’的又一代表人物。”“作为编辑,徐俊在中华书局文化传统接续中,接过了‘守正出新’的接力棒,特别是执掌中华书局十年间,书局的文化影响力、内容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又有了时代新高度。”
克勤在具有良好学术传统和氛围的上古社,从编辑到社长,倾心学术出版,只要和他在一起,话题大多离不开图书出版的人与事。我特别佩服的是,他不仅对图书编辑有许多心得,对出版社生产经营也有很好的见解,也正因为此,他主持出版社任上,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更大提升。我们在“古工委”共事,克勤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遇事果断,有主见。克勤身上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记忆力特别好,喜欢谈上古社历史上书与人的来龙去脉;一是工作之余写作特别勤奋,他应该是我们四人中出版著作最多的,好像退休二三年中,就出版了好几本书。克勤与人相处随和,容易接近,这一点,我们社好几位年轻编辑都有同感。
“诚拙容虚四友斋”
戎默:听说您们各自都有一个斋号,这些斋号的由来分别是什么?
徐俊:退休后我们四个人新建了一个名为“诚拙容虚四友斋”的小群,“诚拙容虚”就是我们四个人的斋号组合。我得号“容斋”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业余写字的缘故,一次写到署款时旁观者问你没有斋号吗?我抬起头看到书架上的《容斋随笔》,就随手加署了“容斋”,很长时间觉得用古代名人的斋号甚是不妥,程毅中先生都打趣问我,你也要写“随笔”吗?转念想既然有《室名别号索引》这样的书,古今同号本是常见之事。认真说,读书人的斋号都不是随便起的,跟父母所赐的大名不一样,是一种自我认同,也可以说是自身性情的外在标识。“诚拙容虚”,立诚守拙,其容若虚,将之视作我们共同的意愿和自我要求,当无不妥。“诚拙容虚”四斋文集,正是本书最早动议的起点。
宫晓卫:关于斋号,徐俊兄用我们四人的斋号建了个“诚拙容虚四友斋”微信群。相对其他三友,我的斋号“虚”取得最晚。因三好友早有斋号,在一次友人聚会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阚宁辉先生建议我也该有个斋号,于是我的斋号遵命而取。
取“虚”为斋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虚”作为二十八星宿之一,按古人说法其所主之地为青州,青州乃是家慈故里,于我有纪念意义。而且二十八星宿之“奎虚”二宿主齐鲁,此前我曾把这两个字用在自己一本小书的名称里。当然,《易》云:“君子以虚受人。”这是“虚”的“谦虚”义,我很看重。
高克勤:读古人书,追慕前辈流风余韵,也想取个斋名。我生性笨拙,父母取名之意,就是希望勤能补拙,所以曾以“补拙斋”为斋名。继而自谓半辈子尚勤快,拙则依然,已知天命,不如顺性一任其拙,于是定名“拙斋”,并公之于拙著《拙斋书话》。
姜小青:我在拙著《诚斋文录》(广陵书社,2023年)后记中,对此有一个记述,这里就转述吧:“至于书名,确实是个难题,总怕名不副实,所以一直拖到最后。我从未给陋室起过什么雅号,只是对‘诚’字一向心存敬畏,犬子也以‘诚’字单名。十多年前,友人西泠印社出版社总编辑江兴祐兄好意,请西泠印社吴莹女史治‘诚斋’印,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朱天曙兄又书赐‘诚斋’,本次姑且风雅一回,用于本集书名,但考虑到内容庞杂,原拟用‘杂录’,后经黄松、曾学文二位仁兄鼓励,斗胆不避古人、前贤,题‘诚斋文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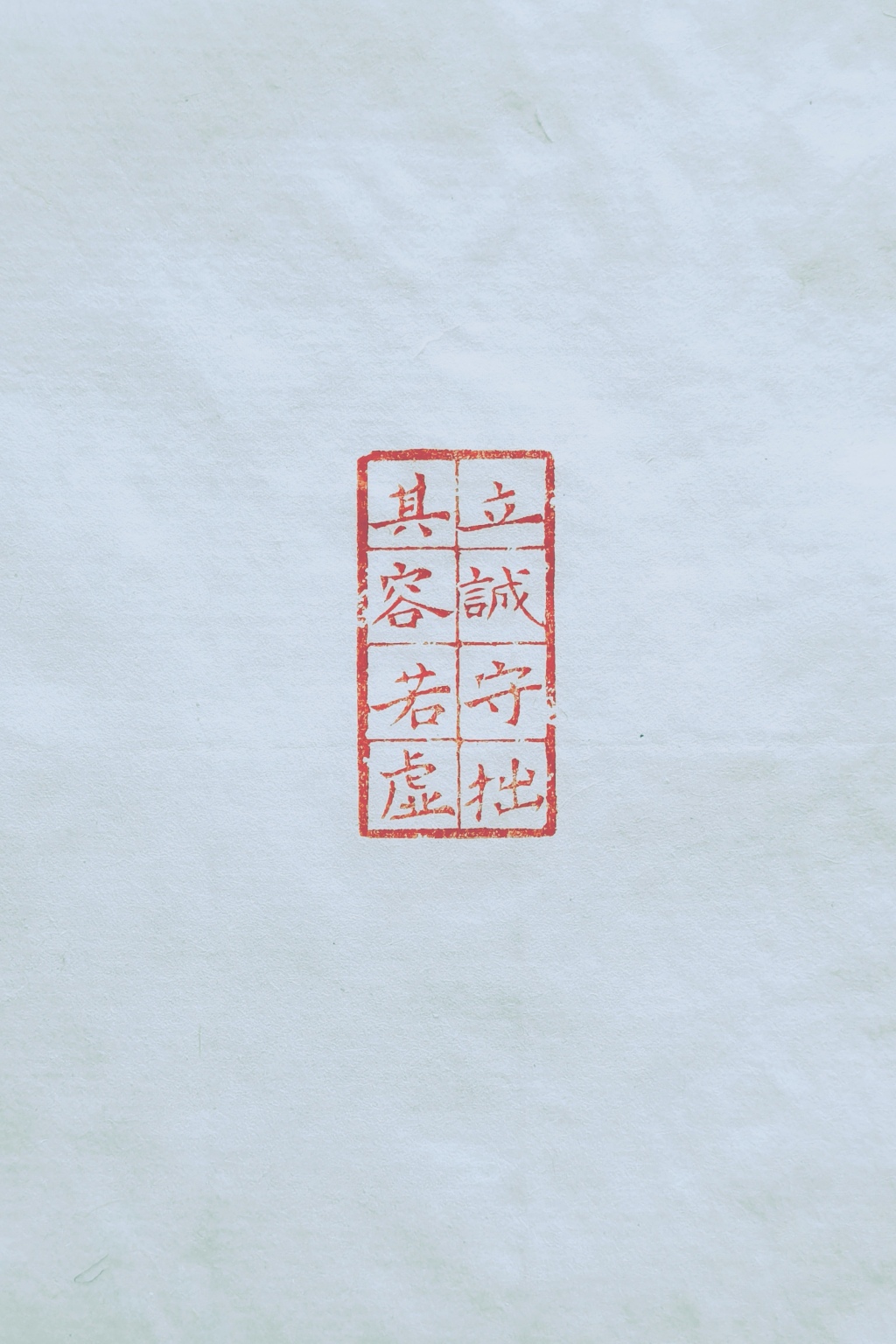
立诚守拙,其容若虚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丨立诚守拙,其容若虚——古籍出版四人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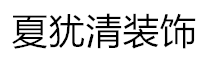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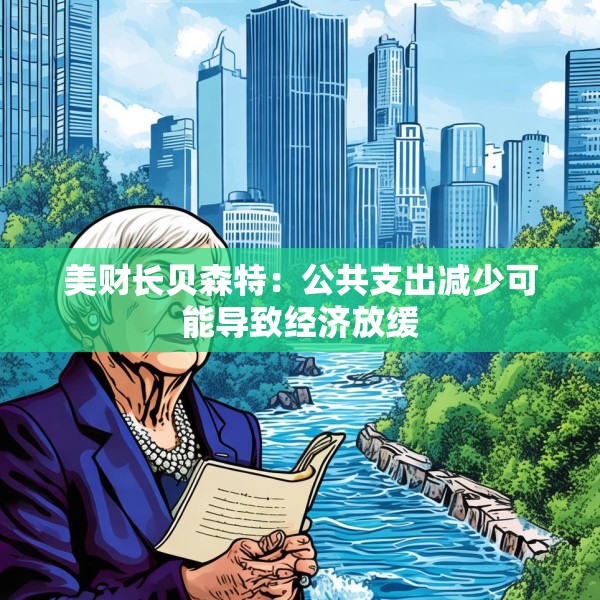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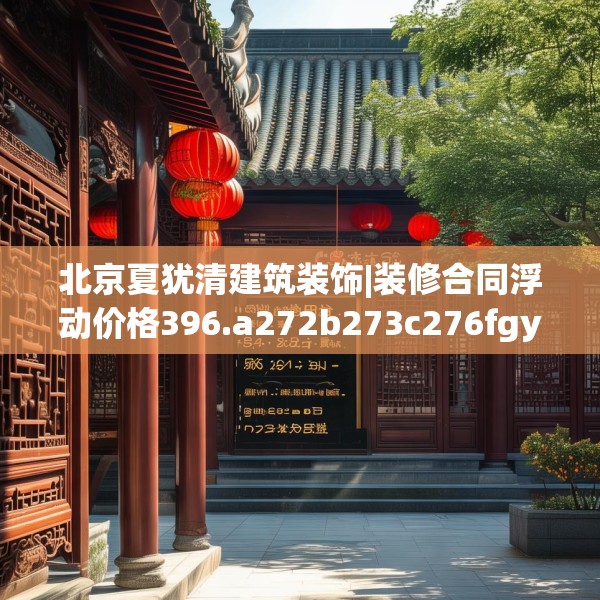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0
京ICP备2025104030号-20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