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到访美国,但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从1989年7月到1992年1月首次访美,其间先后在普林斯顿和耶鲁,整整待了两年有半。尤其在普林斯顿的头一年,更是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是于1989年7月18日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航班,途经东京转飞美国纽约。同行的,是我校科社所的胡广元老师,他是学外语出身转政治学,系根据我校(华中师范大学)同雅礼协会的合作协议,赴耶鲁大学访学一年。因当时的特殊情况,从北京飞东京那一段,全部乘客就我和胡广元等几个人,享受了超级服务,到东京后才有大量乘客登机。说来很不好意思,这次乘机,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呢,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
经约15个小时的飞行,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后,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出机场,就遇到了大麻烦。在机场同胡广元告别后,我拎着两个大皮箱,站在大厅出口候车处,左等右等,也不见原先约好来接我的黄文林——他是武汉水生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普大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大约两个小时过去了,已近深夜十点,在一位热心的美国人的帮助下,我使用投币电话(当时尚不知手机为何物),不断往他住宅挂电话,却始终没人接听。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叫停一辆出租车,让他送我去纽约的中国总领馆,想在那里暂住一晚再做打算。谁知这位黑人司机很不地道,先说知道中国总领馆在哪里,驶上高速公路后,又推说不知道,无奈之下,只好让他直接送我去普林斯顿。车开了近两个小时(因要东兜西转寻找地方),凌晨时分,我们才终于找到了黄文林给我的那个地址。司机向我讨要车资220美元(平时搭乘巴士去纽约来回只需车费30美元!),人生地不熟,加之夜深人静,看他也挺辛苦,只好如数照付。按当时出国换汇规定,我总共就带了300美元,如此就只剩下80美元了,这80美元要支撑到资助我的机构汇来第一笔资助——估计得三周左右,着实心疼!见到黄文林后方得知,原来这位老兄将我搭乘的航空公司名称给弄错了,在机场转了几圈也没能接到我,只好开车原路返回——这在如今普遍使用手机的时代简直像天方夜谭!
尽管阴差阳错没能接到我,但黄文林在我初到美国时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不仅让我暂时借住在他从校方租下的公寓中,而且十分热心地开车带我去附近超市购物,指点我办理各种报到手续。在我最为拮据之时,还慷慨地借钱给我购买生活必需用品,使我能渡过难关。由此可见,初到国外时,来自留学人员的帮助是多么重要。我至今仍十分感念文林兄当初所给予的慷慨相助!
初步安顿下来后,我方有余暇认真打量我所落脚的普林斯顿。普林斯顿是一座幽静的小镇,坐落于纽约和费城之间,因普林斯顿大学而名闻天下,爱因斯坦也曾长期生活于此。普林斯顿大学规模并不大,本科生有近六千人,研究生三千多人,总共就万把人,素以小而精、质量高著称,堪称贵族式精英大学,培养了无数名人和一众诺贝尔奖得主。普大校园景色美得让人心醉:中世纪风格的古典建筑群旁,池水粼粼,草地一片翠绿,四周绿树成荫。我们所居住的宿舍,位于校园边缘的森林之中,格外宁静。从住处到主校区,要经过一大片松林。我经常独自穿行于林中小道,四寂无人,空气中弥漫着松果的香味,时有松鼠的身影跳跃而过,恍若置身世外桃源……
这样的居住环境固然好,但最大的问题是购物太难。偌大的普大校园中,只开有两三家商店,且价格昂贵;小镇上也没有几家像样的购物中心,多的只是咖啡店、小吃店。要购物,必须开车去远处的大型购物中心。只有这时才能体会到,在美国生活,会开车有多么重要!好在开初有黄文林和其他留学生时不时开车带我去购物,一次性买一大堆食品,将冰箱塞满。直到约半年后,花一千美元,从留学生王小荣处买了辆日本产的二手车,才彻底解决了购物难题。我学开车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为了不过多耽误别人的时间,利用夜间,跟随黄文林到停车场学了三次,便大着胆子自己将车开回了宿舍,途中还数度会车。两周后便可在老司机陪同下上路驾车(按照新泽西州的交通规定),一个多月后,顺利通过笔考和路考,轻松拿到了驾照,便可独自驾车了。
待在普林斯顿,好处是僻静,坏处是太僻静,极易使人感到孤独。这大概是许多身处异乡的留学人员都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刚到普大时,学校仍在放暑假,校园内冷冷清清,基本见不到什么人。黄文林的导师带着全家到欧洲度假了,将整栋花园洋房交由黄文林代为照应,他又拉上我一同居住。文林的工作在实验室,每天早出晚归(经常工作到深夜),这样,大概有将近一个月,偌大的洋房基本是我一人独居,成天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群松鼠在草丛中嬉戏,还时不时大胆地窜到门口来觅食,与我四目相对……如此时间长了,难免感到孤寂,勾起浓浓的思乡之情。国内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同家人、朋友生活在一起,多热闹啊!记得当时最怕听到电话铃响,一片寂静中,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因为英语尚未过关,接还是不接,对我是个大问题。接吧,担心听不懂;不接吧,又怕是房主人或黄文林有什么事要交代,因此格外折磨人。
好在学校很快就开学了,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那种难熬的寂寞很快也就过去了,更多的是新环境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我的接待人林蔚教授(Prof. Arthur Waldron)不仅带我参观普大校园,还同意让我使用他的办公室(他主要在家做研究,不经常来办公室),给予了极大方便。我当时主要在研究教会大学史,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宋史专家刘子健教授(他也是章开沅先生的老朋友),对我十分关心,经常嘘寒问暖,还同林蔚教授一道,在校园中央最漂亮的花园餐厅设宴招待我,令我如沐春风。
为了帮助新来的访问学者尽快融入美国社会,普大国际学者学生中心(International Scholar and Student Center,简称IC)还专门为我们安排了接待家庭(host family)和英语教师(tutor)。替我指定的接待家庭是Dpalski一家。这家人非常热情,在约定的日子将我接至家中,叙谈并共进晚餐。谈话范围非常广泛,互相了解家庭情况,又谈到有关东方宗教和艺术问题。原来他儿子马克是学绘画的,对中国画和中国艺术很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夫妇还开车带我去一个家庭烤肉聚会,参加的有来自加拿大、匈牙利、南非、以色列、中国、日本的学者和学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聚会,除主人准备的饭菜外,大家还每人各自带一个菜,在绿茵茵的草坪上边烤肉边聊天,其乐融融,我带去的红烧豆腐大受欢迎。我的志愿英语老师名叫查理·丹尼森(Charles Dennison),曾在华盛顿联邦教育部任职,已退休好些年了,热衷于做推广英语的志愿者工作。丹尼森先生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第一次见面,便为我制定了详细的英语进修计划,让我从阅读一段文章开始,逐字纠正发音。每周三上一次课,从不缺席。在他的帮助下,我的英语口语进步很快,不久便可以初步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这位丹尼森先生是我在美国遇到的道德高尚、最能秉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杰出人士之一。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我至今仍十分感恩他!
除林蔚教授和刘子健教授外,在普林斯顿,我接触最多的还有罗兹曼和余英时两位大教授。罗兹曼(GilbertRoizman)是著名社会学教授,他同布莱克教授发起的普大现代化比较研究项目,在学界享有盛誉;罗兹曼还主编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布莱克不幸于1989年猝然离世后,罗兹曼接手主持该项目,还专门开设了一门这方面的讨论课。征得罗兹曼教授同意,我参加旁听这门课。罗兹曼教授平时话不多,但对我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却非常客气,经常征求我的意见,并表示希望能同罗荣渠和章开沅先生进行合作(章先生来普大后,也应邀参加了他的这门讨论课)。正如章先生回忆录中提到的那样,罗兹曼教授的讨论课因经费充足,还提供免费午餐,经常能吃到可口的中餐,因此听课者踊跃。
余英时先生系从耶鲁转至普大东亚系,主攻中国思想、文化史,学问贯通古今,是当代华裔学者中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在普大期间,我有幸参加旁听英时先生开设的中国思想史选修课。上这门课的,除博士生外,还有好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老外旁听,英时先生一律欢迎。余英时先生的授课,史料丰富,思路清晰,于中国思想史的大关节处,每每有精辟之论,发人深思。余英时先生也很有幽默感,记得一次他正在讲解王阳明思想,突然天色大变,漆黑如墨染,阴风四起,英时先生谐曰,“不好,王阳明鬼魂来也。”引来一片笑声。我当时正研究“绅商”问题,英时先生的大作《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抓紧机会向他请教,经常于课后到其办公室聊天,他给予我许多指点,叮嘱我一定要留意明代汪道昆编撰的《太涵集》,里面有不少有关绅商的史料。我回国后能很快写出专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同英时先生的点拨不无关系。英时先生为人谦和,温文尔雅,乐于提携后进,听说我次年还将赴耶鲁访学一年,主动提出可引荐史景迁教授作为我在耶鲁的接待人,并为我写了推荐信。去了耶鲁后,我与英时先生也时有联系。临回国前,他还寄来两本刚出版的回忆录《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本赠我,一本托我转交李伯重的父亲、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因李埏先生早年也曾受业于钱穆先生,与英时先生是同门。2021年英时先生去世时,我没来得及写悼念文章,写下这些,权作对这位史学大师的无限追思和感恩吧!
在普大,我也有机会结识许多学有所成的青年学人。其中就包括如今声名大噪的王汎森、罗志田两位。汎森兄到普大后即师从余英时先生,志田兄先是跟随林蔚教授攻读博士,林蔚离开普大后转至英时先生门下,亦属其正宗弟子。两位中,我与汎森兄时相过从,得到他许多帮助,但接触更多的,还是志田兄,因我们办公室相邻,又是四川老乡。志田兄禀赋优异,文史功底扎实,但尤为刻苦用功——可能是我所见过的学者中最为刻苦者之一。他常常在办公室一待就是整整一天,潜心治学,中午用微波炉热热带去的盒饭,吃完接着用功,早出晚归,从不间断。他今天能在学界获得“罗大师”之誉称,成为学术大家,绝非偶然。当然,志田兄的成功,也离不开夫人黄老师的呵护,黄老师贤惠能干,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将老罗照顾得无微不至,令我等非常艳羡,戏称他享受的是“民国学者待遇”,好像至今仍如此。
在普大期间,我最为欣赏的还是名校浓郁的学术氛围。校历上会公布每学期的各种学术活动,只要你愿意,这些活动通常都可随意参加。因此,时常有听不完的学术讲座,各种论坛,名人演讲,异彩纷呈,应接不暇。检阅我的简短日记,发现仅11月14日这一日,日程就非常紧张:上午11:00-12:00时,听余英时先生课;12:00-13:30,IC(国际中心)招待会;13:00-16:00,参加著名华裔经济学家周至庄教授主持的学术研讨会;晚上20:00-22:00,夜校英语课,报告“耶鲁印象”。此外,各种学术会议也很多。新学期刚开学时,林蔚教授就组织过一次小型的教会大学史学术讨论会,是在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Nassau Inn)中举行,陈时伟、陶飞亚等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林蔚教授还在郊外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过一次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会议。我之所以记忆犹新,是那个会议中心很特别,是一座豪宅,院子很大,好像是哪位富豪捐赠给普大的,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管理,去了自己开会就行。王汎森、罗志田等都出席了那次会议,我和北大张寄谦老师、陈时伟兄是搭汎森兄的车去的,回来也是坐他的车。我也曾独自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黄宗智教授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讨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问题,会上还遇到了周锡瑞等著名学者,收获甚大。
首次访美期间,有几件趣事(或冒险之举),记忆犹新。
某日,同黄文林、王小荣等一道开车去纽约,逛了唐人街等著名景点,返回之前,天色已黑,想“方便”一下再上路,谁知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厕所。刚好路过纽约警察局,突发奇想,何不就上警察局去“方便”一下。说明情况后,站岗的警察很开通,立马同意了,但需经过安全检查。就在安检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余人都安全通过,只有黄文林怎么也通不过,所有能掏的东西都掏光了,警报器还是一直响,警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称他可能是个“金属人”(metal man),也只好放他进去。事后分析,有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在实验室做实验,头发上沾了什么金属物质,没洗掉。
一次,时值年尾,天气很冷,我同张寄谦老师一同去纽约,出席亚联董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结果搭错了地铁线,提前在邻近RiverSide(亚联董所在地)的黑人区下了地铁,需要步行穿过该区。这一带可以说是纽约治安最差的地段,平时连警察都不怎么敢进去。果然,只见一群类似流浪汉的人,正在那里焚烧废弃的汽车轮胎取暖。见到我们两人后,他们便围了上来,语气很凶地问我们来自哪里,是不是日本人?我们连忙回答来自中国,是中国人。一听我们是中国人,气氛马上为之一变,他们伸出大拇指,一迭声地说“中国人,朋友,朋友!”并很热情地指点我们如何去River Side。到达亚联董后,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说我们真幸运,如果被认定是日本人,那就麻烦了,因为当时美国工人——尤其是黑人,普遍认为是日本汽车等制造品大举进入美国,夺走了他们的饭碗,保不准就会出什么乱子。
还有一次,记得那天正好是美国的纪念日(Memorial Day)假期,我和夫人叶桦(她刚来美国探亲),还有罗志田夫妇等,一道去附近的景点参观,由我开车。当时还没有今天的卫星导航设备,开车全靠看地图(通常是由同行的人看——如果有的话)。当途经一圆盘形地带时,同时有好几个路口,车上各位有说该走这个路口,有说该走那个路口,七嘴八舌,我也一下子糊涂了,心想就照志田兄说的走吧(他毕竟头脑管用),于是开进了他指的路口。殊不知这是一条单行线,只能出不能进,对面开来的车见状,大鸣喇叭,一律靠边给我们的车让路,使我们安全驶离了这条路,拐上大道。事后真是吓得直冒冷汗。志田兄还帮我总结经验:“方向盘在你手上,开车一定要自己拿主意,不能瞎听旁人的指挥。”——实乃高见也!我也是,怎么就忘了他那时还不会开车呢?
另外还有一桩事也同开车有关(严格讲是车祸),令我终生难忘。那时(1990年8月),章开沅先生刚来美国,我们兴高采烈将他接到普林斯顿,暂时安排住在傅雅芳租住的一套宽敞住宅内,陈时伟也从哈佛过来拜见章先生,师生重逢,分外热闹。聚会完后,时伟好像是要去芝加哥,由我开车送他去灰狗站(长途汽车站),路上我们一直在聊天,当从一个路口驶上高速公路时,没注意到竟有一个Stop标志(须充分停车,仔细观察后才能驶上高速路),像平时那样,直接就开上去了。结果,后面快速驶来的一辆货车,瞬间从侧面将我们的车撞向路边,还好,车在栏杆旁停了下来,没有翻越栏杆,摔到另一条恰好从桥下穿过的高速路,否则,我们就一命呜呼了!很快,警车和救援车辆都驶来了,发现我们两人竟平安无事,只是惊魂未定,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检查后发现,货车毫发无损,我的车左面保险杠被切掉一个角,前轮胎被戳破了。警察判定如双方同意,由我自行修车了事。我是主责,当然只能接受。车被拖到修车行后,换个轮胎,没想到居然还能照旧开回去。这事最令我感动的是,事后不久,我开着刚修好的车去章开沅老师住处帮助搬家,尽管事故痕迹仍很明显(尚未上油漆),但先生仍毫不犹豫地上了我的车,说人没出事就好,并夸奖我心理素质稳定,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能照常开车,而且好像比平时开得还好些。后来读章先生的日记才知,他其实是很担心我的,可能是为了宽慰我,让我尽快从事故阴影中解脱出来,才这样说。
……
回想起来,初识美国,有两点最深的感受:
一是当时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大大落后于美国,起码有五十年左右的差距(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相差一百年!)。美国已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国家,而我们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初到美国时所见到的车流滚滚的高速公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在大都市)、琳琅满目的大型超市、丰富多彩的体育和娱乐设施,无不使我内心大为震动。我夫人曾算过一笔账,在美国打一周工的收入,大体相当于在国内工作一整年的收入。如此大的差距,不能不迫使我们思考,中国到底要如何做才能缩小差距,迎头赶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舍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二是当时的美国社会文明程度很高,法治观念很强,井然有序,还基本抱持当初驱使他们的祖先移民北美大陆的清教徒价值观:积极进取,乐于助人,善待新移民。而对中国人的态度特别友好——当然,这同中美两国当时正处于重建友好关系的蜜月期(尽管有短暂的反复)相关,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说你是中国人,大都会得到热情的对待。我们就曾得到许多美国朋友的真诚帮助,也去过许多美国家庭做客,相处甚为融洽。当然美国社会也有自身的许多问题,如大城市犯罪率很高,贫富悬殊甚大等,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这便是我们当时对美国的初步印象。
……
1990年9月1日,我们收拾好行李,告别普林斯顿,驱车驶往纽黑文,开启了在耶鲁的新的访学生涯。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马敏︱初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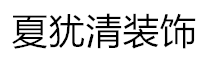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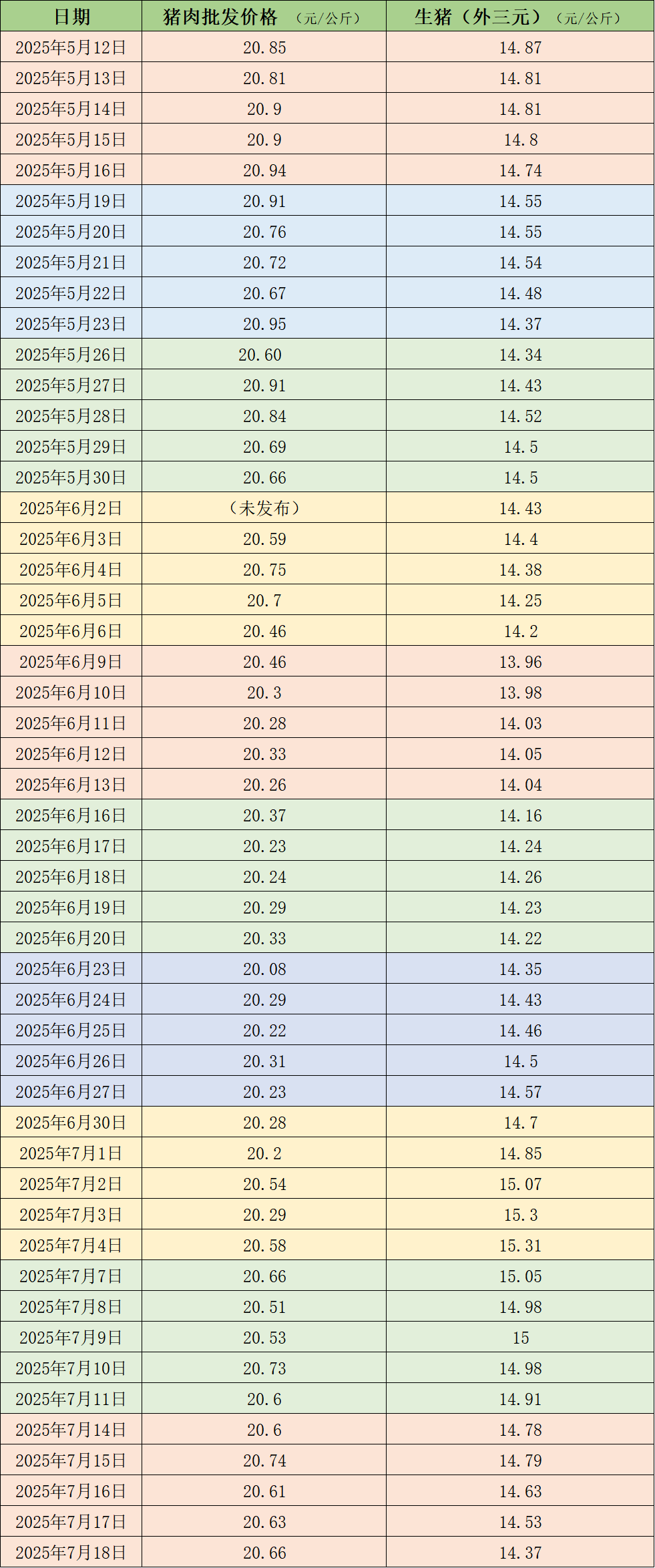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20
京ICP备2025104030号-20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